行业|中国短剧席卷美利坚
 4395
4395TikTok Shop东南亚源头卖家出海峰会,正在报名
““霸道总裁”不远万里迷倒了美国人。
2023年以来,继网络文学、网络游戏之后,短剧成为中国第三样出海成功的文化产品。《2024年短剧出海市场洞察》显示,已有200多款中国短剧 App 投放海外市场,累计下载量近3.7亿次,收入达5.7亿美元(折合人民币41亿人民币)。
对美国人来说,这个东西最早叫“mobi”,这个词是“mobile”和“mini”的结合,指“在手机上观看的迷你剧”。后来,它又被称作 short drama、mini drama……一段迷惑期后,好莱坞业内统一了它的名字:“vertical drama(竖屏剧)”。
这个在美国影视业横空出世,提供大量就业岗位、创造大量市值的新生事物,正是我们每天打开手机就能刷到的短剧。
世界不停地改变。2025年,“霸道总裁”不远万里迷倒了美国人。美国人的生活也开始需要“甜宠”“逆袭”和“打脸”的慰藉了吗?
我们采访了美国的短剧生产团队,从制作端看,他们比我们更规范、更专业主义,劳工权益更受保障;从受众端看,他们和我们遥相呼应:庞大的人口基数,割裂又固化的阶层,越来越混乱的价值观。
美国短剧的幕后,是剧变中压抑的中国留学生,以及找不到工作的美国演员。两个边缘群体齐心协力,用一个个泼咖啡、摔东西、好人即刻好报、坏人即刻天谴的镜头开辟出一条奇异通道,连接了中国与美国,以及两边共享的那些重要但隐形的社会情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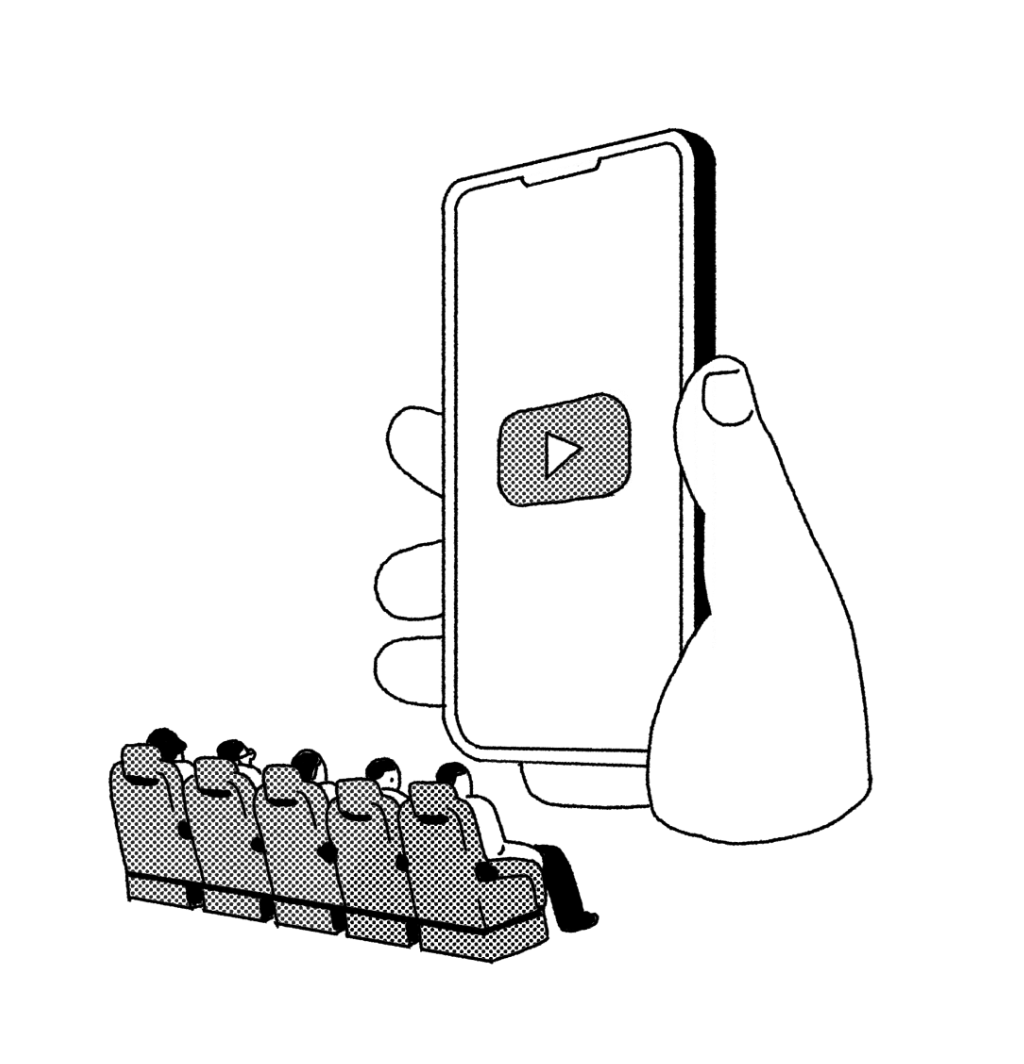
美国导演和演员的短剧修养
要将一种美国人没见过的东西引入美国,势必经历“重新教育导演和演员”的过程。
中国的制片人孟然会给美国的导演开一个大约一两小时的会,展示一些国内短剧的重点桥段,分析短剧的基本属性以及拍法。其中一个重点难点在于,向表演风格含蓄的美国人解释:为什么打耳光的戏是不可或缺的,为什么女主角保持扑克脸是绝对不行的(有美国演员向制片表示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里没有砸东西掀桌子)。对翻拍国内原版的短剧,他们会给美国导演播放原版作为参考。
美国的导演水平也参差不齐。在中国,一个水平不行的导演可能会在片场说:“给多一点!”“笑大一点!”而在美国,一个平庸的导演可能也会喊:“More!”“Smile bigger!”
大部分时候,美国短剧的质感看起来比国内短剧要好一些,这是灯光和服道化部分的功劳。在美国的影视行业,打光通常会获得更多的重视。
不过,美国的导演们显然还不太熟悉竖屏的镜头语言。保险起见,他们会先大量使用定镜头。一次,一位中国的制片人要求他们“加些镜头运动”,她很快发现,这些美国导演习惯性地使镜头“横向运动,而不是垂直运动”。拜托!但这是竖屏。
对这些新晋短剧导演来说,他们只有一些简单的规则要牢记:
机位必须是正面的。侧面的、45度、30度都不行——任何带角度的镜头,都会损失演员面部最直接的情绪。
光要亮,被认为更有质感的暗调光不被允许——观众不是在电影院看剧,他们很可能是拿着手机,在一个日常光很亮的地方看剧。
在一些重场戏上,情绪的爆发可以和上下文断裂,但必须饱满、极致——这些重场戏叫作“投流戏”,它更大的作用是吸引观众点击跳转链接,而不是作为完整的内容链条中的一环。
总之,时刻谨记产品的逻辑,而非内容的逻辑。按产品逻辑,制片人的两大任务,一是省时间,二是省钱。
一部短剧全集时长大约是一部电影的体量(70-100分钟),需要压缩在7-10天内完成。演员提前一天才能拿到剧本,一天需要拍摄10集左右、15-20页剧本,这是美国人没见过的节奏(在国内这个周期会更短)。一部美国短剧的成本只有30万美金左右,而一部美国长剧的正常投资大约在几千万美金。一家长剧公司一年也许只会做两三个剧,一家短剧公司一年可以做200个剧。
首先被改变的是工时。一般来说,美国影视行业从业者的每日工作时间被限定在8小时内,最多不能超过12小时。超过8小时的部分需要与演职员协商,且时薪需要上调。而在中国,短剧一天通常会拍到15-18小时。
拍摄美国短剧时,大多数公司都会满打满算地拍足12小时。像 ReelShort 这样的头部大平台能基本做到不超过12小时。如果超时了,也能保证加钱。而市面上更多小的短剧公司和一些承制,有时会拍到15-16个小时。
“在合法的边缘试探。”一位美国短剧从业者告诉我。另一位坚决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访谈对象则说:“有时候省钱省到了违法的程度。”
违法可能包括:拍摄没有许可证,不给员工上保险,不走正常的劳务合同,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。
一个美术部门工作人员的时薪,按照工会最低标准应该在30-40美元。一个决心要“合法”的短剧剧组给出的时薪是16美元。这刚刚高于纽约州的最低时薪标准。更多情况下,这个数字会更低。

当然,美国的短剧片场还是有一些国内没见过的东西,比如,“亲密戏份协调员”。这个角色的工作是与每一个参与亲密戏份(比如吻戏)的演员沟通,确定每个演员能接受的尺度和界限,确保不会有人感到不舒适。有的亲密关系协调员已经参加了上百部短剧的制作。
2024年年底,一批美国演员被运到中国,在中国的场地拍摄,以节省成本。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,被选中的拍摄地包括广东珠海与山东青岛。这两个地方能提供与西方非常相似的外景。


Ryan Vincent 是一个工会演员,他演艺生涯的高光是在奥斯卡提名影片《金发梦露》中出演一个配角。在演短剧时,他为自己取的艺名叫 Jack Fierce(凶猛的杰克)。他说,这个名字是一个玩笑,“一个剧烈的意象”。Ryan 说,名字能使他与角色融为一体。他已经演过近十个霸道总裁。
美国的短剧片场很有趣,Sam 形容那里像一个“游乐园”,由于一天要拍10-12页的剧本内容(传统剧集项目一天只拍2-3页),他可以“尽情发挥”,有时觉得“演爽了”。哪怕是那些为参与短剧制作感到羞耻的人,在拍摄过程中也会觉得“玩得很开心”:长片项目片场通常严肃沉郁,而在短剧片场,你经常能见识到宴会厅里一群美国演员围成一个圈,被主角转着圈挨个打脸。
“It’s silly.(它很傻)” Ryan Vincent 说,他指的是那些扇耳光、泼水的戏份,“我觉得它很有趣,但它确实很傻”。不过,他非常肯定地告诉我,在经济上,短剧是一个重要的产业,它为好莱坞像他这样的演员提供了60%-70%的就业岗位。
一些演员担心过参演短剧会成为“黑历史”,但思量再三,仍选择参演。影视业是一个“薪水低、但有 glamorous(光环)的行业”。美国演员工会共有16万成员,其中只有2%-4%的人,可以仅靠演员这个职业维持生计。也就是说,有10万以上的演员,还需要做别的工作维生,譬如在空余时去餐厅做兼职。
一种职业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:让自己工作起来。“你是想成为一个(一直在等待的)演员,还是一个有工作的演员?”Travis 说,“谁会获得这个 Netflix 的工作,是我还是格伦·鲍威尔(好莱坞当红影星),我的意思是,好吧,我一点机会都没有,对吧?所以我的角色被缩减为越来越小的部分。”
他们努力自我教育:作为一个演员,你不必去评判它,只需去完成它。即使剧情与自己的想法有冲突,也应该用专业的沟通方式去解决,而非闹情绪。
孟然为这份工作感到骄傲。在美国可以使用母语工作,她认为这是一种“特权”(privilege)——不是每个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可以说母语、找到一个民族文化强势的产业,拿到一份高薪的收入。
“中国资本硬生生地在美国杀出了一条赛道给华人做。养活中国人也养活美国人。” 程铭说。他是另一个南加大的毕业生。
也有人怀着隐秘的羞耻。一位访谈对象坚决不允许我们提到她的名字,她觉得“太丢脸了”。除了故事的价值观落后,更糟糕的是她觉得自己输出了太多“中国人做事的方式”。她称自己为(加引号的)“中国文化大使”,增加了一些“bad reputation(坏名声)”。
有些人产生了更复杂的感慨。纪录片导演王逸飞说,北美短剧有时使他想起日本六十年代的“粉红电影”——它们的共同特征是,在萧条的时期,以一种下沉的方式,为这一行业保留人才。
他见过不少短剧导演试图在拍摄短剧时“夹带私货”。比如,大家都知道短剧的最后10集是没人看的,因此,他们会在最后10集里加入一些奇怪的调度、打一些不寻常的光,甚至搞点“一镜到底”。这些尝试有时会被资方默许,有时则会被“打回重拍”。
“质疑短剧,理解短剧,成为短剧”,马克说。刚开始从业时,按照习惯,他让灯光师打了质感更好的暗调光,很快他遭到资方的批评,并被勒令重拍。两年来,他隐约觉得自己理解了一些新的东西。这似乎是一种堕落,又不全然是,甚至不全然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自洽。他见证了这个行业最初的混乱,也见证了它逐渐变得规范起来。他读过完全粗制滥造的剧本,也参与过稍微精良一些的制作。他至今也不喜欢看短剧。但当他因为职业的专业度受到同剧组成员的认可时,他也感受到了“成长”。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感受降临在了他的肩上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““霸道总裁”不远万里迷倒了美国人。
2023年以来,继网络文学、网络游戏之后,短剧成为中国第三样出海成功的文化产品。《2024年短剧出海市场洞察》显示,已有200多款中国短剧 App 投放海外市场,累计下载量近3.7亿次,收入达5.7亿美元(折合人民币41亿人民币)。
对美国人来说,这个东西最早叫“mobi”,这个词是“mobile”和“mini”的结合,指“在手机上观看的迷你剧”。后来,它又被称作 short drama、mini drama……一段迷惑期后,好莱坞业内统一了它的名字:“vertical drama(竖屏剧)”。
这个在美国影视业横空出世,提供大量就业岗位、创造大量市值的新生事物,正是我们每天打开手机就能刷到的短剧。
世界不停地改变。2025年,“霸道总裁”不远万里迷倒了美国人。美国人的生活也开始需要“甜宠”“逆袭”和“打脸”的慰藉了吗?
我们采访了美国的短剧生产团队,从制作端看,他们比我们更规范、更专业主义,劳工权益更受保障;从受众端看,他们和我们遥相呼应:庞大的人口基数,割裂又固化的阶层,越来越混乱的价值观。
美国短剧的幕后,是剧变中压抑的中国留学生,以及找不到工作的美国演员。两个边缘群体齐心协力,用一个个泼咖啡、摔东西、好人即刻好报、坏人即刻天谴的镜头开辟出一条奇异通道,连接了中国与美国,以及两边共享的那些重要但隐形的社会情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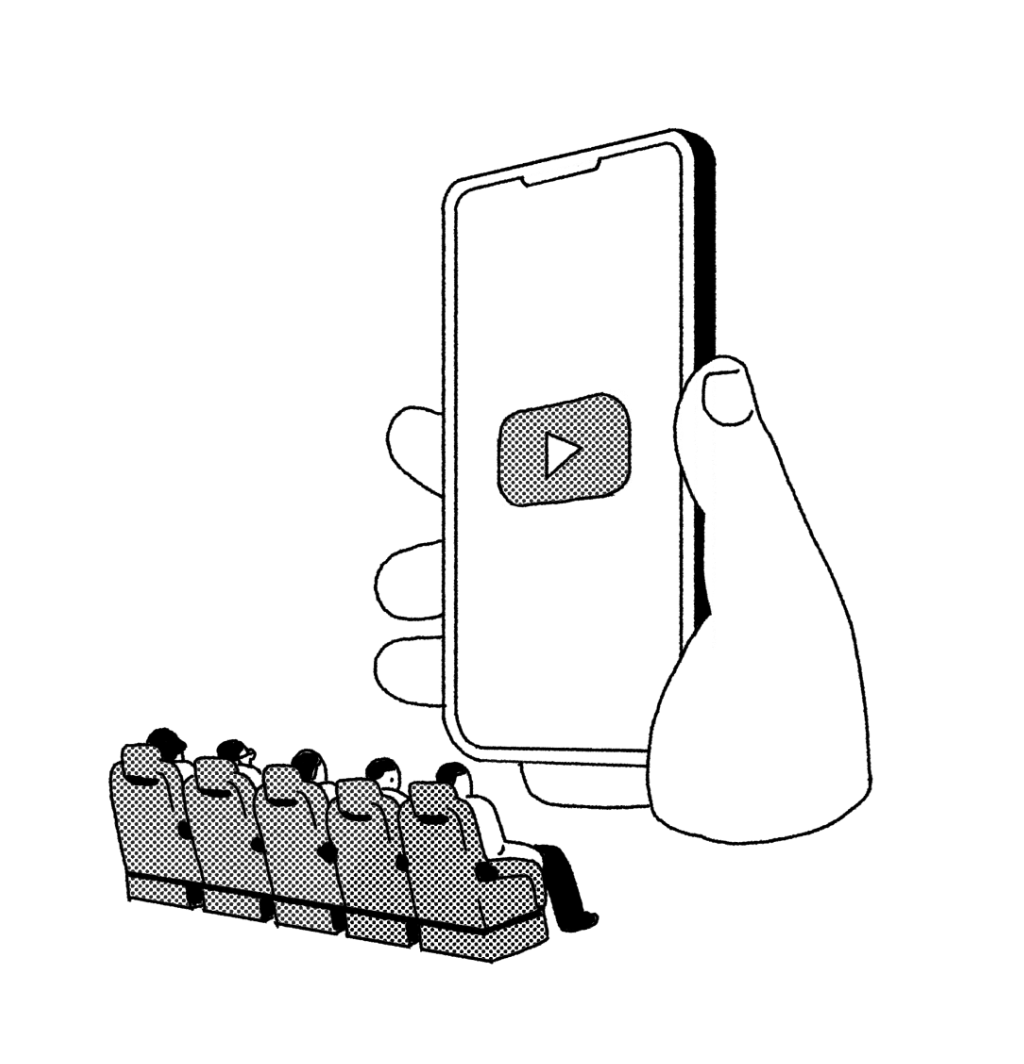
美国导演和演员的短剧修养
要将一种美国人没见过的东西引入美国,势必经历“重新教育导演和演员”的过程。
中国的制片人孟然会给美国的导演开一个大约一两小时的会,展示一些国内短剧的重点桥段,分析短剧的基本属性以及拍法。其中一个重点难点在于,向表演风格含蓄的美国人解释:为什么打耳光的戏是不可或缺的,为什么女主角保持扑克脸是绝对不行的(有美国演员向制片表示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里没有砸东西掀桌子)。对翻拍国内原版的短剧,他们会给美国导演播放原版作为参考。
美国的导演水平也参差不齐。在中国,一个水平不行的导演可能会在片场说:“给多一点!”“笑大一点!”而在美国,一个平庸的导演可能也会喊:“More!”“Smile bigger!”
大部分时候,美国短剧的质感看起来比国内短剧要好一些,这是灯光和服道化部分的功劳。在美国的影视行业,打光通常会获得更多的重视。
不过,美国的导演们显然还不太熟悉竖屏的镜头语言。保险起见,他们会先大量使用定镜头。一次,一位中国的制片人要求他们“加些镜头运动”,她很快发现,这些美国导演习惯性地使镜头“横向运动,而不是垂直运动”。拜托!但这是竖屏。
对这些新晋短剧导演来说,他们只有一些简单的规则要牢记:
机位必须是正面的。侧面的、45度、30度都不行——任何带角度的镜头,都会损失演员面部最直接的情绪。
光要亮,被认为更有质感的暗调光不被允许——观众不是在电影院看剧,他们很可能是拿着手机,在一个日常光很亮的地方看剧。
在一些重场戏上,情绪的爆发可以和上下文断裂,但必须饱满、极致——这些重场戏叫作“投流戏”,它更大的作用是吸引观众点击跳转链接,而不是作为完整的内容链条中的一环。
总之,时刻谨记产品的逻辑,而非内容的逻辑。按产品逻辑,制片人的两大任务,一是省时间,二是省钱。
一部短剧全集时长大约是一部电影的体量(70-100分钟),需要压缩在7-10天内完成。演员提前一天才能拿到剧本,一天需要拍摄10集左右、15-20页剧本,这是美国人没见过的节奏(在国内这个周期会更短)。一部美国短剧的成本只有30万美金左右,而一部美国长剧的正常投资大约在几千万美金。一家长剧公司一年也许只会做两三个剧,一家短剧公司一年可以做200个剧。
首先被改变的是工时。一般来说,美国影视行业从业者的每日工作时间被限定在8小时内,最多不能超过12小时。超过8小时的部分需要与演职员协商,且时薪需要上调。而在中国,短剧一天通常会拍到15-18小时。
拍摄美国短剧时,大多数公司都会满打满算地拍足12小时。像 ReelShort 这样的头部大平台能基本做到不超过12小时。如果超时了,也能保证加钱。而市面上更多小的短剧公司和一些承制,有时会拍到15-16个小时。
“在合法的边缘试探。”一位美国短剧从业者告诉我。另一位坚决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访谈对象则说:“有时候省钱省到了违法的程度。”
违法可能包括:拍摄没有许可证,不给员工上保险,不走正常的劳务合同,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。
一个美术部门工作人员的时薪,按照工会最低标准应该在30-40美元。一个决心要“合法”的短剧剧组给出的时薪是16美元。这刚刚高于纽约州的最低时薪标准。更多情况下,这个数字会更低。

当然,美国的短剧片场还是有一些国内没见过的东西,比如,“亲密戏份协调员”。这个角色的工作是与每一个参与亲密戏份(比如吻戏)的演员沟通,确定每个演员能接受的尺度和界限,确保不会有人感到不舒适。有的亲密关系协调员已经参加了上百部短剧的制作。
2024年年底,一批美国演员被运到中国,在中国的场地拍摄,以节省成本。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,被选中的拍摄地包括广东珠海与山东青岛。这两个地方能提供与西方非常相似的外景。


Ryan Vincent 是一个工会演员,他演艺生涯的高光是在奥斯卡提名影片《金发梦露》中出演一个配角。在演短剧时,他为自己取的艺名叫 Jack Fierce(凶猛的杰克)。他说,这个名字是一个玩笑,“一个剧烈的意象”。Ryan 说,名字能使他与角色融为一体。他已经演过近十个霸道总裁。
美国的短剧片场很有趣,Sam 形容那里像一个“游乐园”,由于一天要拍10-12页的剧本内容(传统剧集项目一天只拍2-3页),他可以“尽情发挥”,有时觉得“演爽了”。哪怕是那些为参与短剧制作感到羞耻的人,在拍摄过程中也会觉得“玩得很开心”:长片项目片场通常严肃沉郁,而在短剧片场,你经常能见识到宴会厅里一群美国演员围成一个圈,被主角转着圈挨个打脸。
“It’s silly.(它很傻)” Ryan Vincent 说,他指的是那些扇耳光、泼水的戏份,“我觉得它很有趣,但它确实很傻”。不过,他非常肯定地告诉我,在经济上,短剧是一个重要的产业,它为好莱坞像他这样的演员提供了60%-70%的就业岗位。
一些演员担心过参演短剧会成为“黑历史”,但思量再三,仍选择参演。影视业是一个“薪水低、但有 glamorous(光环)的行业”。美国演员工会共有16万成员,其中只有2%-4%的人,可以仅靠演员这个职业维持生计。也就是说,有10万以上的演员,还需要做别的工作维生,譬如在空余时去餐厅做兼职。
一种职业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:让自己工作起来。“你是想成为一个(一直在等待的)演员,还是一个有工作的演员?”Travis 说,“谁会获得这个 Netflix 的工作,是我还是格伦·鲍威尔(好莱坞当红影星),我的意思是,好吧,我一点机会都没有,对吧?所以我的角色被缩减为越来越小的部分。”
他们努力自我教育:作为一个演员,你不必去评判它,只需去完成它。即使剧情与自己的想法有冲突,也应该用专业的沟通方式去解决,而非闹情绪。
孟然为这份工作感到骄傲。在美国可以使用母语工作,她认为这是一种“特权”(privilege)——不是每个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可以说母语、找到一个民族文化强势的产业,拿到一份高薪的收入。
“中国资本硬生生地在美国杀出了一条赛道给华人做。养活中国人也养活美国人。” 程铭说。他是另一个南加大的毕业生。
也有人怀着隐秘的羞耻。一位访谈对象坚决不允许我们提到她的名字,她觉得“太丢脸了”。除了故事的价值观落后,更糟糕的是她觉得自己输出了太多“中国人做事的方式”。她称自己为(加引号的)“中国文化大使”,增加了一些“bad reputation(坏名声)”。
有些人产生了更复杂的感慨。纪录片导演王逸飞说,北美短剧有时使他想起日本六十年代的“粉红电影”——它们的共同特征是,在萧条的时期,以一种下沉的方式,为这一行业保留人才。
他见过不少短剧导演试图在拍摄短剧时“夹带私货”。比如,大家都知道短剧的最后10集是没人看的,因此,他们会在最后10集里加入一些奇怪的调度、打一些不寻常的光,甚至搞点“一镜到底”。这些尝试有时会被资方默许,有时则会被“打回重拍”。
“质疑短剧,理解短剧,成为短剧”,马克说。刚开始从业时,按照习惯,他让灯光师打了质感更好的暗调光,很快他遭到资方的批评,并被勒令重拍。两年来,他隐约觉得自己理解了一些新的东西。这似乎是一种堕落,又不全然是,甚至不全然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自洽。他见证了这个行业最初的混乱,也见证了它逐渐变得规范起来。他读过完全粗制滥造的剧本,也参与过稍微精良一些的制作。他至今也不喜欢看短剧。但当他因为职业的专业度受到同剧组成员的认可时,他也感受到了“成长”。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感受降临在了他的肩上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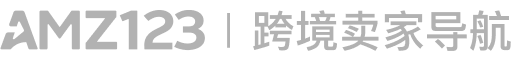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 热门活动
热门活动 
 其他
其他 04-09 周四
04-09 周四
 热门报告
热门报告 










